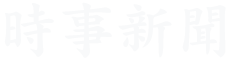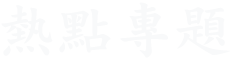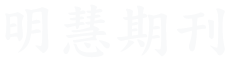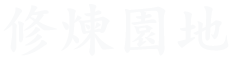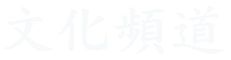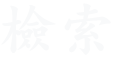家
得法後,短短3~4個月,面黃肌瘦的我變得白裏透紅,精神愉快,精力充沛。大法給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獲得了新生,誰知1999年以江澤民為首的邪惡集團在全國展開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我也不例外。
1999年7.20,我帶著5歲的兒子進京上訪被公安截住,無理扣押一晚上後,第二天被鎮政府人員帶回鎮上,從此我便失去了人身自由,每天要準時到派出所報到,不准到外地進貨。白天,鎮政府派專門人員跟蹤;晚上睡覺,他們就在院子裏或大門口盯梢。每到敏感日他們就半夜砸開門進屋檢查我是否在家。
1999年9月我和其它一些大法弟子在鎮財政所非法關押8天。關押期間,白天挨政府官員的辱罵;晚上不准回家,睡在財政所的桌子或板凳上。後來被強行寫「保證書」注,並交押金2000元後才放人。
1999年11月27日,我因堅持修煉真、善、忍,在派出所大院被罰站一天,傍晚又被戴上手銬,在警車上被遊街後,送到市看守所,在看守所強行寫「保證書」,被像犯人一樣拘留31天並交罰款6000元後才放人。非法拘留期間,5歲的兒子如同沒娘的孩子一樣,幼小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丈夫和親人受到了精神上的痛苦和經濟上的壓力,自己的生意更是受到了很大損失。
2001年陰曆4月13日,我娘家的父母因在家集體學法被市公安局非法拘捕。4月17日,即父母被非法拘捕後第三天下午,我和姐姐、妹妹正在幹活,來了一輛白色麵包車,裏面坐著5,6個鎮上的人,其中一個當官的說:「你們姐妹三到醫院,你們的父母住了院。」我和姐姐馬上想到父母可能被看守所打得太厲害。我倆上了車(妹妹因孩子太小沒去),誰知麵包車沒拉我們去醫院,而是去了鎮政府。一進大院,十幾輛汽車一字排開,大院裏站滿了警察和鎮委人員,嚴陣以待的架式。我倆下車向大門口走去,各自被兩人架著胳膊到了一間鎮辦公室,被八九個人看著。去廁所也有兩個人跟著。我問其中一個女的:「你們到底要把我們拉到哪兒?」她說:「拉到轉化班上去。你們的父母不轉化,讓你倆勸勸他們。」一小時後我倆被帶上車,十幾輛汽車在後面跟著直奔縣城,到了縣城沒去醫院,也沒去「轉化班」,而是奔向通往市中心的路。出了縣城我和姐姐問:「你們要把我們綁架到哪兒去?」他們說:「不用急,5分鐘就到了,你們也就知道去哪兒啦。」不一會兒,車子拐向了火化廠,我可憐的姐姐還不知道是火化廠,以為是「轉化班」。
到了火化廠,院子裏停滿了警車,站滿了警察,偌大的火化廠見不到一個閒雜人員,只有警車、警察和政府人員,火化廠被全部戒嚴。我倆被叫到火化廠辦公室,一進屋發現我姐夫早已等在哪兒,表情非常難看,內心充滿了恐懼。難怪我們一下午沒聯繫上他,原來他早已被他們叫去並沒收了他的手機。不一會兒,我哥哥和二舅也被他們叫來了。我家成員基本到齊後,公安局宣布說我媽在看守所心臟病突發而死亡,因氣溫很高,必須立時火化,我父親現在血壓很高220,隨時也有生命危險。宣布完後,我和姐姐抗議:「我母親沒有病。立即停止迫害大法弟子,立即釋放被關押的父親。」公安局的人說第二天就放我父親回家,然後讓家屬看遺體。
他們早給母親從頭到腳換好了壽衣,頭髮被剪成了光頭,大概是死後剪的,因後腦勺沒剪著,頭頂部有很多麥粒大的紅斑,最大的和玉米粒大。原來紅光滿面,體態很胖的母親瘦了很多,臉上發紫,並且汗洇洇的。因公安局的人看著我們,又給她馬上穿好了衣服,身上有沒有傷,我們沒能看到。原來白白胖胖、身體健壯的母親就被這樣強行秘密火化了。火化完後,已是晚上7~8點鐘,所有的警車和鎮委官員又拉著我們和母親的骨灰盒送回家。鄉親們看著長長的車隊排滿了大街,以為母親回來了,都來看她,沒想到一進屋門看到的是一個骨灰盒:天啊,怎麼會是這樣,三天前從這間屋子裏走出去一個看上去只有50歲(實際年齡62歲)白白胖胖、健康和善的大活人,三天後卻燒成了骨灰裝進了盒子。
當天晚上大部份車走了,留下了兩輛車停在大隊辦公室門口,公安和鎮上的人在裏面。第二天鎮上的歹徒就催著我們趕快入葬。我們堅持按照當地的風俗等5天,即4月20日出殯。公安部在火化廠當眾說第二天即4月18日放我父親回家,可是到了4月20日中午了,我們還沒見到父親的蹤影。午飯後,母親的骨灰盒就要入土了,還是不見父親回家。情急之下,我大聲說:「不放我父親回家,母親的骨灰盒不能入土。」歹徒騙我們說:父親已經回來了,在鎮上,為了父親的身體著想,暫時不讓他回家,等出了殯再回家。我們信以為真,就把母親安葬了。
4月21日,我的哥哥因打擊太大得了精神分裂症,不久後住進了精神病醫院,我的弟弟在外地上大學也因此受到牽連。頃刻間家破人亡,人財兩空。我們全家共被勒索罰款2萬多元,父親又被抄家,現已身無分文。母親去世35天後,我們姐妹三人和父親又被強迫送到鎮610洗腦班非法關押7天,強迫洗腦。
一個社會,如此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它究竟去向何方?
﹝編注﹞署名嚴正聲明將歸類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