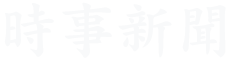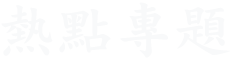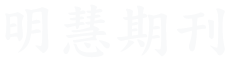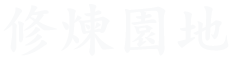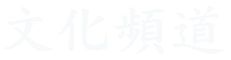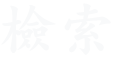與同修探討「猶大」問題(二)
事例二:
我的一位親人乙01年在轉化班上轉化之後我一直見不到她,我從勞教所回來她也沒主動來看過我,我知道躲著我的人一定有問題,後來,好不容易聯繫到她,我發現她其實也很想見我,就是有一股無形的力量阻礙著她。3月我被臨時派到她家附近工作,於是很自然的約見她,這麼方便,她當然馬上就來了,一問她果然一直處於封閉狀態,不看新經文,認為明慧上的經文是假的,甚至她的一些外國朋友說起同情法輪功的話她還想反著給人家講,因為她覺得是煉功人做了不顧身邊人感情的事,而且心裏有仇恨等(她想說的是她自己和她所看到的事實,可這些只是她看到的一些人表面沒修好的東西,不能和大法混為一談,我很慶幸她當時沒說,如果真這麼幹就又是破壞大法。)。
第一次見面我先以很快的速度講了我對法的認識,乙最後說:「你這張嘴真是能說。我還沒見過誰能講成這樣,但是我覺得有些人說不出來,做的很好。」還笑話了我兩句。我知道她言外之意認為沒有一個正法弟子是修得好的,這也不都是她的問題,因為我們沒修成之前的確都還有很多缺點。至於乙的恥笑我根本不往心裏去,你說我好、你說我壞,我都不動心,真善忍才是衡量標準。當時沒時間再講了,我很熱情的說:「以後有機會再聚。」她也很高興的說:「行,有時間電話聯繫。」就分手了。雖然沒有結果,但我並不氣餒,我相信沒白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鋪墊。
後來我又到她單位附近去辦事,很自然的又去看她。一起吃飯時我連續向她講了三個小時,我根本沒想她和我有甚麼不一樣,完全就像是在與一位久別的同修交流、交心,一個故事接一個故事的講,非常自然的娓娓道來,思想中對乙沒有一點間隔和障礙。
這些故事有的是我們自己的事,也有的是我從網上看來的。我在給她講每一個故事的時候都銜接的非常自然,好像沒經過甚麼太多的思索。她一直認真、安靜的聽著,偶爾加半句很高興的評論。但我能感到其實我講的每一個故事都是對她有針對性的,只是那一念來自於思想很深很深的地方,所以,表面上連我自己都幾乎察覺不到,她更不覺得我有任何目地。
講到最後,我講了一些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怎樣證實大法、講清真象的事,她被震撼了,說出了那天最長的一段話,她說:「我聽你講你遇到的事情時,都說得那麼輕鬆,好像都是很簡單的問題。但我知道其實在遇到那種事的時候是不會輕鬆的,如果是我自己遇到就會很難過去。可你好像是一步就把困難給跨過去了!(拉長了聲音還做了個手勢)……」我知道這次她是被善念熔化了,相信修大法的人不但能說的好、做的也同樣好,這是「事事對照、做到是修」的實修結果。我告訴她:「我能過去、不會和常人計較、是因為我心裏想的是證實大法,救度眾生,心是高於常人的,是為別人的,不是為自己的,所以就能很容易的過去。」她說:「我有時遇上矛盾也知道自己碰上了一個硬東西,但我就繞著走,我丈夫說我是茅坑的石頭。我不願再做大法的事也是因為我發現自己只要一做就是在起破壞作用,我很害怕自己做不好,所以還不如不做呢。」
她講出的這個問題是很多人轉化的關鍵所在──他們這部份人正是因為發現自己以前在正法中起了一些負面作用、不願再破壞大法才轉化的,可他們不明白轉化也還是破壞大法。這次我給她講的東西讓她感到震撼,是因為她從來沒想到過原來還可以這樣去講真象,去正法,帶給別人的都是美好,使我們身邊的一切向好的方向去發展,她從來沒這樣理解過正法和修煉的關係,現在乙明白了產生副作用不是因為我們做了甚麼事,而是自己心裏有執著造成的。
我又用「修口」為例講做與不做的關係,並說:「我們如果甚麼都不做,好像表面很平靜,其實執著都被掩蓋著,你現在不也能感到自己仍然有問題嗎?我們去做正法的事,因為帶著人心,可能就會暴露出問題,但暴露出來不用怕,正好利用這次機會修正自己,那麼以後就會用更純淨的心態去做,就會進入良性循環,越做越好……」
她對我得法的過程非常了解,她說她的問題是從始至終沒堅信過大法,我鼓勵她說:「《轉法輪》上說:『到一定時期還給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讓你感覺這個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煉上去,有沒有佛,真的假的。將來還會給你出現這種情況,給你造成這種錯覺,讓你感覺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堅定下來。』師父還說到修煉的最後一步都會有對一個人是否堅定的考驗。既然師父這麼講了,就不只是你的問題,我也在其中,師父提出的是咱們每個人的問題,那我們就得格外認真,都要堅定正信,才能談得上正念。」
最後她要看全部的新經文,從新走證實大法的路。
談話過程很長,我始終對她是平等的心態,沒有說教,只是親切的聊天,經常講一些我如何向內找解決自身問題的事。我甚至沒說一句你甚麼認識是錯的,你怎麼不對,你有甚麼問題,沒有否定,更沒有指責,總之全在講對的東西,結果這些正的、善的、美好的內涵反倒完全感動了她,讓她到最後擦了眼淚。
事例三:
同修丙是和我一起被抓的,在勞教所的時候走的太偏了。剛回家時有些沒被抓過的同修見過她,以後每次見到我都跟我說:「她沒救了。她講的東西太壞了。她回不來了。」我說:「我在裏面曾有一次機會遇見她,她當時能聽懂我說的,也想做好,只是因為時間太短,她回到以前的環境又被別人影響了。」同修說:「我看是不行了。她自己也說不想回來了……」我說:「如果真是不想回來就隨她去吧,師父說:『在魔難中沒有走過來的是人。如果人不行了,那就再造,這也是人的劫數。我是想盡力救度一切世人與生命。人不爭氣,為了掩蓋執著,主動的邪悟。你自己不要未來,那我就放棄你。我沒有執著的。』(《建議》)咱們就做師父要我們做的事,師父都對她不執著,咱們幹嗎要執著呢?勞教所裏像她這樣的也不是一兩個,因為你認識她,就反反復復提她的事,是不是有點執著呢?既然提了,又總說她不行,於事無補,還讓自己心裏難受。如果有機會再見到她,就盡力幫一幫,真的沒機會了也不必多想。」
我沒有主動去找她(後來得知她為了躲開功友們,根本沒住自己家,找也沒用),但心裏一直記掛著她,有想幫她的一念。
一年多以後的一個週末,我沒甚麼事還是想去加班。走在路上,忽聽身後有人喊我,回頭一看正是丙。我如同老友重逢一樣趕緊和她寒暄,我真是記不清是怎麼和她打開話題的,總之非常自然,像聊天一樣,也沒去揭她以前的短,主要講了大家現在的做法,為甚麼這樣做。她很愛聽,於是我們就索性坐在路邊又聊了一個多小時。
我說:「在勞教所裏的一些人比較極端,(我不針對她說,只作為勞教所裏的一種現象說,但她聽了也就能對照出自己的問題),以前很多人把修煉的形式當成是全部的修煉,以為自己只要是在學法、煉功,就是在修煉,並不懂得甚麼是法。在強制的痛苦中想起真、善、忍是法,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說自己只要大法不要法輪功了,不學也不煉了。可是法都不學了怎麼指導自己的行動呢?結果還是做不好。」丙說:「我現在就有這樣的困惑,有一次我發現自己忍不住脾氣,做的還不如常人了。」
我隨手指著旁邊的房子說:「好比這座房子吧,表面看到的是這些牆,我們真住進去了,才知道原來是裏面的這些屋子,這些空間讓我們受益。結果有人明白這個就索性把牆給扒了,可是沒牆了,屋子又在哪呢?而且我們是通過住進這所房子才感受到這些空間,就好比我們學了法輪功才明白大法,如果房子沒了,以後的人住哪呢?總得為將來人著想啊,他們也得來學法輪功才能在大法中修煉。[1]」話不重,但她全聽明白了,說:「是呀,有時我也覺得困惑。現在媒體上所謂的透明度也報出一些天災人禍,我一直在想將來的人可怎麼辦呀?」
我說:「你看這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多可憐,他們生活在一言堂的社會裏,他們連聽真象的機會都沒有。可他們又是來源層次很高的主、王、神。前些天我遇到一位從澳大利亞回來度假的學生,我問她在國外看沒看過法輪功的酷刑展,她說看過,但她覺得不是真的。我告訴她,有的外國人看完說如果這些是真的話,那也太殘忍了。但我要說,中國媒體的報導肯定是假的,但國外功友展示的也不夠真實,因為一些事,比如性虐待沒法拿出來展示,很多會對人體造成很大傷害的酷刑也只能擺擺樣子,再比如罰站、罰蹲、綁死人床等體罰,如果你只是看見一個人站著或躺著,你是根本感覺不到這種痛苦的,但要是十幾天甚至幾十天都這樣那可真是活受罪。我講了看守所、勞教所裏的經歷和見聞……,她聽了驚訝的說你們真是太可憐,他們真不是人!怎麼了,不就是煉功嗎?我們學校的學生就坐在大草坪上煉!丙,你看,這個學生是一個非常善良的孩子,她小時候做好事的消息曾經上過報紙,而且已經出國多年了,可是她還是受了造謠媒體的影響。舊勢力以我們有執著為藉口,發動了這場針對大法的迫害得矇蔽多少無辜的人呀?」
因為我知道丙曾經對同修說勞教所不打人,所以剛才那段話裏我還有意講了一些在勞教所裏的暴行,我沒直接說她說的不對,只把事實告訴她,可這回這位受矇蔽的同修又有所醒悟,很驚訝:「有這樣的事?」
我說:「他們總是弄虛作假。讓咱們從早幹到晚,吃的是讓人浮腫的飯,還說咱們都吃胖了,應該感謝政府關懷。一來人檢查就改菜譜,說咱們每頓好幾個菜,還有扁豆之類的好東西。對外欺騙世人說對咱們是慈母姐妹一樣的關愛。」這些日常生活中的事丙就更熟悉了,丙在勞教所裏總給××黨唱讚歌,可現在被麻痺的記憶終於恢復了,說:「就吃過一次扁豆,還集體中毒了。」
丙講出了她的顧慮:「我現在是不行了。我一本書也沒有,大法在我頭腦裏剩的越來越少了。我當時變成那樣是因為我覺得代價太大,我捨不得失去人世中的好東西,我覺得我比別人自私。」既然已經看到自己的問題,我就善意的向她講明了其中的利害:「人世間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應的眾生,他們抱著希望隨我們而來。比如說我們的親朋好友是我們的眾生,如果我們現在不能向他們講清真象,還按勞教所那一套講,反而騙了他們,那麼他們心中仇視大法,就會最終被淘汰。那時,你會看到你的親朋好友一個個死去,多慘呀。自己沒修好,回去後你的天體殘缺不全甚至全是空的,可到那時你明白這塊空缺應該是你的弟弟,那塊空缺應該是你的朋友……就因為自己在人間貪戀名利情,把親人們全給耽誤了。痛悔也來不及呀!」說的每句話都是為她和她的親人著想,她聽了很感動。
她又說:「可我當時真是全站反面去了,勞教所說的那些壞事我全相信是法輪功幹的。錯太多了,我已經沒希望修成了。」我鼓勵她:「勞教所是個特殊的環境,完全做好是很難的。我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咱們都一樣。師父說『只要堅定的學好法、你能夠改過、你能重新做好,你還是大法弟子。你就重新做好就是了,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如果你思想中把它看得很重,就又形成另外一種悔恨、擔心等壓力的時候,那麼你就又陷在這個執著中了,你又走不出來了。……摔倒了你就爬起來,繼續做大法弟子應該做的。』(《2003年加拿大溫哥華法會講法》)你想你現在是鼓起勇氣跟師父走讓師父滿意,還是趴著好?」她點點頭。
我又說:「可你發現了嗎?你首先想到的是修成太難,說明心裏還是求圓滿,」她點頭,我接著說,「我們現在做的事並不是給自己做的,只是因為眾生太可憐,我們要去救他們,我們的提高是在不斷的為了別人放下自我中無求而自得的。圓滿的目標雖然非常遙遠,但只要是在向那個方向邁進,終有一天能走到。我自己經歷特殊,所以我早就沒有圓滿的概念,在我看來,就是遇到一件事就儘量做好一件,沿正路一步步走過去,肯定是那個目地地。這樣一段42公里的馬拉松被拆成了420份,每份不過100米,你就覺得每一段都很容易。而且師父絕對是好的留下,壞的去掉,即使沒達到圓滿,修成多少算多少,你也明白如果再隨波逐流,後果是甚麼。」
她聽著不斷的點頭,說:「你今天講的讓我非常震動,看來今天能遇到你,不是偶然的。」丙終於決心要重新開始,分手前我們互相留了電話,她說:「這是我頭一次把我的電話告訴功友。」
我離開勞教所前險些被延期,多少和丙有些關係,但既然她已經明白了,我隻字未提那段經歷,我只希望走錯路的同修還能按師父要求做。師父都不記過往之過,只要他們想歸正,我當然可以忘記別人所有的錯,但我會記住別人全部的好。分手前我真誠的說:「當初在看守所真是多虧你們這些大姐照顧我這個小妹。我要好好謝謝你。」她直推辭:「嗨!我照顧你甚麼了?是你沒水喝,還沒白沒黑的教我們背經文,別看我是92年學的,就我學的那點法,要不是你幫我補了很多,後來肯定會更糟。」
[1]有些轉化的、邪悟的人,把法輪功和大法說成兩回事,故此處有此說法,主要是針對丙在勞教所裏學的「糊塗帳」進行清理,並向正面引導。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