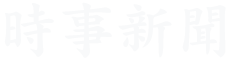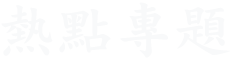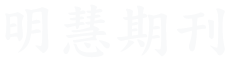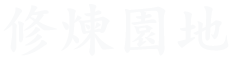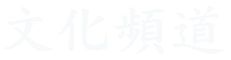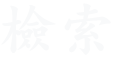濟南興隆村農民徐延江屢遭迫害的經歷
徐延江是農民,家裏不富裕,一九九九年以後多次被綁架、勒索迫害後,在濟南「天泰太陽樹」房地產的物業上幹活。今年五月,他免費發放神韻晚會光盤被所謂的「發到了上司手裏」,被他在「天泰太陽樹」的領導所謂「錄了像」,然後「天泰太陽樹」的領導就告訴徐延江「錄像了」,讓他自己寫「辭職報告」。徐延江於是失去了工作。
徐延江,八月四日被濟南市公安局市中區分局所屬的桿石橋派出所綁架,已經是他第四次被綁架迫害。此前他因「進京」和向民眾講清真相、傳播法輪大法的美好曾被綁架三次,被非法「拘留」三次,被非法「勞教」一次,被非法「勞教」未遂一次,被勒索錢財兩次,並遭受了強迫放棄信仰的洗腦迫害和無數次的謾罵、毒打。
以下是徐延江自述他十幾年來所遭受的迫害(其中部份法輪功學員的名字已隱去):
我今年六十四,我原來一身的病,通過學大法好了的。我九八年開始學大法的。學大法以前,我原來有肝炎、血脂稠、咽炎,失去勞動能力五、六年多了,光在那裏玩,我還住過院,一天三把藥吃。
一、第一次進京的經歷
那時候第一次是俺和村裏的四個人去的北京。到了一個私人商店,過來一個便衣問我:「煉法輪功的吧,跟我走吧」,就把我領到廣場分局。那裏還有這麼些同修呢。有在鐵籠子屋裏的,有在背法的。一會兒去了一個人問我:「你是哪裏的?」我不告訴他。他挺奸猾,說:「知道你是那個濟南的。」我說:「你怎麼知道呢?」這樣他就確認了我來自哪裏,然後把俺們都分到「山東代理處」──陶然賓館。
在陶然賓館,一個三十多歲、一米八多、身材略胖的人問我:「你是哪來的?」我說:「從天上來的。」他就穿著皮鞋一下子踢我的鼻樑根,把我的鼻樑根踢骨折了。我當時穿著楞(濟南話,「很」的意思)白的褂子,那血都淌上了,還淌了攤在地上那麼些血。他踢的時候,一邊踢一邊說:「叫你從天上來的」,這一腳正好踢在鼻樑根就骨折了,淌了老多血,他看差不多了,就說:「洗洗去」。我說「沒事啊」,他就給你叫你洗去,洗了洗結果發現白褂子上那個鮮血啊,一點也沾不上。
後來它們就給俺鎮上(山東省濟南市十六里河鎮)、村裏(興隆村)打去電話,到半夜這塊兒就有人去了,去了住的「陶然賓館」,住在那裏。第二天早晨把俺拉回來的。
拉回來本地以後直接就上的派出所。從派出所裏,又把我弄看守所去了,在看守所待了31天。關了我31天放出來以後,又弄聯防(「聯防」是派出所下面的一個分支,甚麼也管,和派出所是一夥的)上去,「罰」了每個人都是5000塊錢。當時是把我單獨的放看守所裏,她們(和我同去的法輪功學員)回來的,都「罰」了5000塊。他們知道我沒錢,借了3000塊錢給他們。他們知道我沒錢,叫俺在聯防上的兄弟們給他們拿去3000塊錢到派出所裏,在「聯防」上給了他們,他們說是叫「保證金」甚麼的,說以後再給不再給的,也沒再給。
二、第二次進京的經歷
這樣回來又到了二零零零年十月份,十月三號,我覺得還得該去北京。俺幾個商議商議,就又去的。第二次是十月份,俺村裏七個去的。第二次是二零零零年十月三號晚上去的,那時候「聯防」上還在二環南路十字路口上擺上桌子,下著雨,在那等著(防止我們村的法輪功學員進京)。
我們七個人到了天安門廣場上,看到那裏人山人海的。
它(村裏)知道俺們走了,就又找了北京去了,到了那裏以後又空車回來的。
第二次從北京回來以後,正好過秋呢,隨著俺在地裏正幹著活呢,「聯防」上開著一個麵包車拉著上地裏就找我去了,叫我去「聯防」。到了聯防上,我先去的,然後是另一個同修去的,在那等了得兩個多小時。「聯防」上說沒甚麼事了想叫我回去呢,一會兒去了個電話說「不行,不能叫他回去」,就拉著上了派出所了。
一開始去派出所,他們說「先在這放著你,以後才那個甚麼呢(指動粗等恐怖手段)」。到了派出所裏等了一會兒,就把幾個和我一起去北京的女同修拉了去,上了西郊張莊拘留所了,才去的時候下著雨。拉去拘留所的理由是「進京了」。
三、拘留和勞教迫害
(一)拘留迫害
到了拘留所裏,第十來天上去了幾個便衣,也不知道是幹嗎的,專門「提」的我。
張莊拘留所有兩排屋,兩排屋間相隔二三十米。便衣把我叫到了前面這排屋裏去,他(便衣)叫我跪了水泥地上,我沒配合他,他就用手掌搧我這個頭,搧了一巴掌。結果震的他這個手抖摟開了,抖摟最後他又用拳頭夯我這個頭,反正夯的、打的這個聲音啊,他們(其他被關押的人)都在屋裏,隔著窗戶、隔著十來多米這麼遠都聽見了。那時候關著的大部份都是煉法輪功的,好幾百人啊,窗戶挺亮的,他們都聽見了都看見了。就是我跪那裏,錘我那頭、臉都發了青了,反正震他手也震的不輕。最後甚麼我也沒回答他,他說「老頑固啊」(當時五十一週歲),就叫我回來了。
從看守所十五天,緊接著又拉到鎮裏去給俺開了個會,各村的有去領的。把我和另一個女同修又關了派出所那個籠子裏。第二天又把俺倆用一個手銬銬起來,又送到劉長山看守所裏去了。
看守所、勞教所、洗腦班都在這裏,都在這個「劉長山看守所」這裏,前後院。
送到看守所裏待了十六天,關到十二、三天這塊兒裏,那個警察給了我一張紙,告訴其他人說:「誰也別管他,他願寫甚麼寫甚麼。」給我一張紙。俺也不會寫字兒,啥也不會寫(內容),寫甚麼?我就寫了一個字:「煉」。A4的紙吧,這個「煉」字兒寫的挺大,給了他,給了他過了一天還是兩天,就隨著就把我「勞教」啦。
(二)勞教迫害
「勞教」就是先到派出所,派出所裏姓麼來那個副所長,他說「怎麼著啊老徐,你要是再不甚麼(指迫使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可是三年啊」,我說「三年不就千數天嘛」,我說我要不煉這個功我就沒命了,我原來一身的病,通過學大法好了的。他說「那我就沒辦法了」。
這樣呢,就在派出所籠子裏關了我一天,第二天弄著我上了警官醫院去查體去。查體戴上手銬,在那查了體,就拉了我劉長山勞教所裏去了,到那還得再查體。那個醫生說:「各項都合格啊」,我說「煉法輪功的沒病!」那個警察說啊:「你要再說話就揍你!」
這樣就勞教了,關了屋裏。這一天成立的「法輪功中隊」,我記得是楞清楚,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七號我進去正好第一天成立「法輪功中隊」。第一天都見了同修,那時候農民啊就是我,還有章丘一個,俺兩個是農民。
第一天晚上都在那裏交流,到了第二天早上都在那裏煉功。到了晚上呢,值班的警察就彙報了(學員們交流、煉功的情況等)。到了第二天一開會,就「敲山震虎」的「震」啊。
到了第二天晚上,一過了十二點,就開始值夜班的警察啊,才上來時一個鐘頭上屋裏去一次,再是半個鐘頭,再是五分鐘,再就不出來了,就在屋裏不出來,就害怕在那集體煉功。一看也沒有帶頭的,有一個同修叫張天寶,他先帶的頭,起來的。起來那個值夜班的警察啊,就想弄著他走,這個同修也和他爭論,它想拉他吧,俺這伙都起來圍住那個警察啊,不叫弄著走。他一個人值夜班他弄不了走啊,僵持到明天。
這樣吃了早晨飯、警察上了班,就把他(張天寶)弄出去說是「問他去」。關他那個走廊的通道是伸縮的鐵門啊,都關死,俺這伙都聽著有打人的聲音,俺們走在走廊裏,聲音楞洪亮,俺們就咋呼「不許打人,不許打人」,喊聲灌滿了整個的樓。
它使用了一個甚麼辦法呢,它說「你看見打人了嗎?你過來看看。」它先叫年輕的,光看了出去是看不見回來。一會兒也叫看看去,去了好幾個都回不來。一個個的往外「提」都「受審」去啊。有些人就是因為這樣承受不住就簽字了(指放棄修煉法輪大法的「保證」等)。
到了第三天,挨著我了,直接弄我辦公室裏去,戴上手銬,年齡大的留到最後。
戴著手銬正好下著雨雪呢,弄了小號裏去,去了這麼一堆警察,我也沒數,反正得五六個,一個人一根電棍。帶我去的那個叫「教導員」啊,它的名叫祝照熏,拿出個本子,它說:「你看人家都寫了,簽的名說是不甚麼(指在強迫下不修煉大法)了,你寫不寫啊?」我說這不是真的,俺不寫。它說「不寫啊,趴下!」那時候我穿著一個褂子在看守所裏,在看守所裏連個拉鏈都給扭了去,這個在看守所裏呆過的都知道,敞著個懷。它們叫我趴那個水泥地上,戴著手銬,它這伙都電我,有電頭的、電脊梁的、電腿的、同時一塊兒電的。電一會兒,拉起我來,說:「寫不寫啊?」,我說:「不寫」,它說:「不寫再趴下」。這樣電了三次。我這個頭啊頭髮不是少嘛,剛推了頭,和這個貓叨的似的這個血就淌開了。
淌(血),那個叫祝照熏的那個「教導員」一看甚麼了(指看到流血了),電了第三次上,就說「行了行了行了」,這麼拉起我來,又叫我到水管子上洗了洗。
回來,在那個樓北邊邊那個南甚麼那個窗戶都敞開開。我這個銬子啊,把我銬在、掛在窗戶鐵稜子上,我這樣背著,背著褂子翻啦著。那個值夜班的警察,咱心話(「以為」的意思)演那個《便衣警察》可知道這個警察心眼還挺好啊,我說:「同志我這個手給我背著來,你給我正當正當。」,「好,我給你正當正當!」,它把我提溜起來掛了上層那不是有個橫撐嘛,吊我那頂上啦,我腳呢,正好夠著地。我肚子不是拉鏈沒有嗎,貼了那個牆上,敞開窗戶,到了10點來鐘,沒吃飯還。從那一甚麼了,從「體罰」這個同修開始都絕食不吃,三天。
到了晚上10點來鐘,那個「教導員」說:「人家那個誰誰誰都吃飯了,人家都吃了,你還不甚麼呢,不信你看看去。」它是指一個管財政部門的教授學員,叫葉景倫。我過去一看,他真吃了。人家吃咱也吃吧,我也吃了。
沒轉化的、沒簽字的俺六個格外關著,他們簽了字的(指在酷刑逼迫下所謂「放棄修煉」的)呢,楞「自由」,隨便睡覺各自關著。
過來那個勁,俺七個都一塊兒。(迫害者)單獨的派上幾個裏頭那個犯錯誤的其他被勞教人員,看著俺、管著俺,跟俺這伙要錢。俺沒錢,就是有一個濟鋼的他有錢。就是知道了以後沒給他(指其他被勞教人員知道了這個濟鋼的人有錢,但此人沒有給他們錢),(那些被勞教人員)還揍人家。
這樣光俺七個,吃的饅頭是從前那個「飼料糧」,就是捂包(濟南話,「捂壞了」的意思)了那糊的(濟南話,「那樣的」意思);鹹菜就是個人種的蘿蔔,裏頭都黑心了、空了,腌的還辣乎乎的。反正俺七個給了一個鹹菜,使個調羹挖著,一個人一塊,在那吃黑饅頭。
還「罰」俺七個跑步、踢正步等,一個七十歲的都摔了。
當時一個同修叫張興武,十幾天沒叫睡覺。
還有一個小伙子姓劉,絕食三四個月,最後把他單獨關著弄了三樓上去,說是「他跳樓了」,從衛生間裏「跳下來死了」。還去的警車去照相甚麼的,都是假相,怎麼死的誰也不知道。
還有一個叫李武堂的,是濟南三中教政治的老師,他是最堅定的,一直不「轉化」,把他和其他刑事犯關一塊兒,還超期關押。李武堂被那些「邪悟」的人治(濟南話,「欺負」的意思)的很痛苦,痛苦的都喊開警察了。體罰的辦法包括撓腳心、揍人等。
這樣待了十一月份過了年,正月十五之前去了一趟王村,又拉了來三十三個同修,帶了連被子加人一車拉了來的。從王村拉到濟南劉長山勞教所的三十三個同修都是濟南的。原來俺那裏是二十四個人,拉來三十三個,來的時候傍黑天了,也是有點朦星下著小雨。叫他們夜裏休息,來了叫他們「改善改善生活」,吃了點好的。
後來它是「幾個人包一個人,幾個人包一個人」,就是逼著你叫你「轉化」。一個個的時間不一,有五六天的,有六、七天的,一個個的「轉化」了上那邊去,沒「轉化」的故意讓你在那走廊裏凍著你。
「轉化」的手段是:不叫你睡覺(「熬鷹」);車輪戰術;放詆毀大法的電視、小本本;上課洗腦。
有個叫宋號鐘的是最邪悟的一個頭子,原來的學員景旭斌轉化了也挺邪惡。
在裏頭待了26個月。「自然減」,本來誣判三年,不同程度去了三個月,又放回來。
四、在自己村裏遭受的迫害
戶口從派出所轉到勞教所去了,放回來我就沒戶口了。沒戶口都給消了也找不著,十六里河派出所最後又重新給落的。
「敏感日」的時候「聯防」上的人不斷去找我去,晚上12點多都打電話騷擾我。
到了2008年,不是要開「奧運」嘛,「聯防」又找我,要辦「換身份證」。「聯防」上找我很多很多回。我是怎麼想的呢:你邪黨,我身份不用你來證實。我說「俺不辦,俺沒錢(20塊錢啊)」,它一趟一趟的找我,著急了都。才上來是好說「拉著你去,再送回你來」,我說「你拉著俺去俺也不去,俺沒錢,俺不去,俺沒用處」。他三個幹「聯防」的一趟趟的找、打電話,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了這個身份證。
到了08年開「奧運」,又開始找。這一次是晚上把我叫村裏去,在那裏有五、六個人,有一個都喊他「王警長」是甚麼,穿一身黃衣服派出所那種衣服。其它的都穿便衣,也有「610」的,其中有「610」那個滕學魯。我幹活回來他在那裏問我:「你幹的麼活兒呀這一燜(濟南話,「這段時間」的意思)」,我說「甚麼也幹唉」。上屋裏去,他說「你這臉面不孬啊」,我說「煉功煉的」。它就開始嘿唬我,他拿出他對待犯人那個勁頭來點點劃劃的嚇唬我。點劃我我也點劃他,氣的他不輕快。我說:「我也不是犯人,我也不是甚麼,你點劃我我也點劃你!甚麼事兒啊你這麼點劃我。」最後他不點劃了,我也不點劃了,問我說甚麼「沒事啦,走吧」,我也沒走。呆了一會兒他說:「真沒事了,走吧,回去吧」,這麼走的。
到了09年不是開全運會(指2009年在山東省濟南市開的「全運會」)嘛,又叫我上那個村長辦公室裏去,還是那個滕學魯。我說了幾句比較平和的話,結果過了幾天,兩三天吧,他們上俺家去了。在院子裏,我把他讓到屋裏去。他看見屋裏放著師父的法像,就拿起來,我說「這個你不能動」,他就放下了。又打電話又叫去幾個,結果把我的書搶奪去好幾本。
五、二零一零年底再一次被綁架和勞教迫害
(一)在齊河被綁架到看守所迫害
二零一零年底,我和兩個女同修去給人家送年曆去,開著那個三輪車,到了齊河表白寺。我在三輪車上,過來一個麵包車,敲了敲那個窗子,說:「下來下來下來」。
下來後把俺三個人弄到了表白寺那個派出所裏,在那裏把俺那個錢、手機都叫俺掏出來。問我是哪裏的,我不說。他打了電話給晏城公安局,打了電話去了,把俺三個分開,俺三個都不說。
後來他弄個A4的紙,就是和我一塊兒去的一個女同修的照片,它說是從網上調出來的,黑白的,他怎麼弄出來的咱不知道。他說:「你認識她吧?」,這樣就知道俺是誰了。
後來拉到晏城一個叫「防暴大隊」的地方。俺們的錢都給他掏了去了,他給俺買了一個燒餅吃。8點多弄了俺到看守所裏去的。
弄看守所裏去,去了讓脫衣裳,脫的一點也不讓穿,換上他那個衣裳。另外兩個女同修,女警察叫她兩個屋裏去。我呢,叫了我屋裏去,給了一個破黃秋褲,上邊扯到腿根,下邊光一個邊,搭到膝蓋的一個秋褲。還有外邊一個外套,也都扯了的,要多麼髒就多麼髒。冬天零下九度這麼冷,光給個這個穿,一個黑襖,楞小、楞薄(很小、很薄),裏面也不是棉花,也不讓扎腰。
早晨是吃一個小饅頭,中午是吃兩個。菜是白菜幫,連四成熟也沒有,頂上皮上那個膩蟲一層黢黑,下邊那個泥巴那個土吃完了很多。「青菜」白菜幫子也不多,一個個的漂著,連個鹹菜也沒有。
去了不讓睡覺,那裏頭那個犯人讓幹活,做收音機上那個三極管那些玩意,他這伙都是有定額的,幹不完這一宿不讓睡覺。
第二天讓俺睡覺了。那個黃被子摟吧摟吧的(濟南話),一提溜起來那個棉花都掉出來,就和那個透亮的是完全一樣。(棉花)都上一個角上去,這樣給這麼一床破被子。就在那個水泥地上、水泥台子搭上一個纖維板,就給這麼一床破被子連鋪加蓋的,冬天零下這麼冷。
挨著「值班」的時候,我是「值」十點至十二點,過來一個看守所裏的「教導員」一個老頭子得為(濟南話,「故意」的意思)狐假虎威的說是我煉功,說:「煉功呢,讓他走,讓他出去!」,弄著我去戴上腳鐐。
那個腳鐐是又粗又長的鐵,中間裏一個環,銬腳脖子的是和大拇指那樣的「16」的鋼筋,這個腳鐐得十五、六斤。叫你銬上,嚇唬你,叫上院子裏來回跑啊。跑,它兩個鐵棍中間一個環根本邁不開步啊,他說他還嫌你走的慢,叫一個犯人拉著走,來回的得一百米長、一百米遠。他拉著你走,拉了兩趟,走了兩遭,把這個腳脖子都磨得破了都磨破了,回來,待下午收拾收拾又換一個旁的號裏去,就是老弱病殘的號,上那裏去。
第二天早晨我起來煉功的時候,一個嫌疑犯起來上廁所,看我煉功呢,一巴掌就把我鼻子給我扇破了,扇的鼻子呼呼淌血,臉也青紅了。他小便完了回來,又給我一巴掌。兩巴掌搧的太重了,他倆把我提溜起來,一個提溜腳鐐的,一個提溜手銬的,把我拽了床上。我躺了那裏,仰著是抱輪動作(法輪功第二套功法的煉功動作)。那警察來了說「給他搬下來!」,搬下來我再拿上去啊。
這樣早上上了班以後,打我的那兩個嫌犯走了。就是打我的這天,他倆走的。
這樣又呆了四天,我這個腳脖子磨的可疼了,晚上睡覺白黑的戴著,就這麼薄被子,一挪地方、一翻身、一下床就疼,不敢動啊,我就咋呼(濟南話,「大聲說」的意思)叫給我解開。也不解。戴了一個星期,給我解開了。
(二)第二次勞教迫害,未遂
之後,一直到了二零一一年初,皇曆臘八這天,叫我上辦公室裏去,戴上另一種腳鐐和手銬,連著的,非法枉判了我一年半勞教,叫我去章丘那個王村去勞教。
戴上腳鐐和手銬去了。去了一查體,在胸透的當中,一查不合格,剛出來給我個口罩了,一下子給倆。給兩個口罩咱也不懂得,去了又上旁的,有檢查的。到了那裏,人家說:「這個不行。」到王村勞教所那裏說「不收」、「不合格」。
又拉著我去查,齊河縣公安局裏的又花了500塊錢,還走的後門。回去還是不行,說身體「不合適」,不行。
這時候就晌午多了,又去了一家查「艾滋病」這一類的,又回去了,還是不行。
連著查體這三次,這時候都黑天了。到了快到齊河看守所這塊兒裏,那個齊河縣公安局的曹姓警察說:「老徐,回去不能亂說,就說嫌年齡大叫回來了,別說旁的!」,我沒做聲。他說「聽見了嗎?!」快到門口了,曹姓警察說:「把口罩拽了(濟南話,「扔了」的意思)!」,我就拽了。去了那個警察正好想走呢,曹說:「這個回來了,嫌年齡大,不要」,我說:「不對,我是查出來甚麼病甚麼病!查的是肺結核啊!」,我說:「你看看」。嚇的看守所那個警察說:「你離我遠著點,遠著點!」
關我那個小號裏剛進去,我跟那個值班的嫌犯,他因車禍關在裏面,我說:「給我留出飯來,還沒吃飯來」。後來關我小號裏,單獨隔離。剛鋪好了,又叫我回到原來關的屋裏去。
待到皇曆十一,把我放出來的,勒索了1000塊錢,理由是「查體」之類。要5000,說沒有;又說「少了3000不行」,最後給它1000塊錢,我回來了。(自述完)
請關注在中國大陸持續了長達十三年的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屢次的被綁架、被謾罵、被虐待、被勞教、被勒索錢財……徐延江只是被迫害者中的一名,他至今仍被非法關押,被非法剝奪著作為一個人所應具備的最起碼的人身自由。
警察們,法官們,檢察官們,公務員們,天天關注明慧網的「610」們……無論你是誰,請你在和家人享受你那略顯豐厚的福利待遇之餘,拷問一下自己的良心:看著這一個個活生生的案例,你們真的還能漠視下去,自己騙自己的主動接受中共邪黨的洗腦?就因為擔憂失去那一點只是高於大部份中國同胞的稍微豐厚的「俸祿」而強迫自己相信「這樣的事情很正常」,然後再繼續渾噩下去嗎?
像徐延江這樣的法輪功學員,在那樣的生存條件下,義無反顧的向中國大陸民眾傳播真相是為了甚麼?真的像中共邪黨給你們洗腦的那樣,是因為「受國外反華勢力的控制,想要打倒共產黨」嗎?共產黨還用得著法輪功學員打倒嗎?它們自己的一切都在打倒著自己,現在已無可維繫。它掌握著龐大的國家機器和軍隊卻仍惶惶不可終日,懼怕著手無寸鐵的法輪功學員。因為民心早已喪盡,所以愚蠢的中共邪黨只能以「維穩」為第一要務,它越「維」越不穩,它亂象叢生、天災人禍,敗象凸顯,去日無多,可短視的追隨者們卻依然慎重。
大法修煉人心中有大法,他們修煉「真、善、忍」,沒必要去跟那邪教中共較甚麼勁。徐延江講真相是為了你們,法輪功學員們不顧一切的講真相也都是為了你們。因為天要滅中共,「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明白真相、退出邪教中共你們才能得救,不隨其覆滅。
請了解真相吧!不要辜負了法輪功學員們所做的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