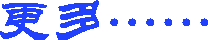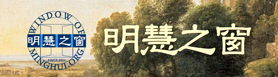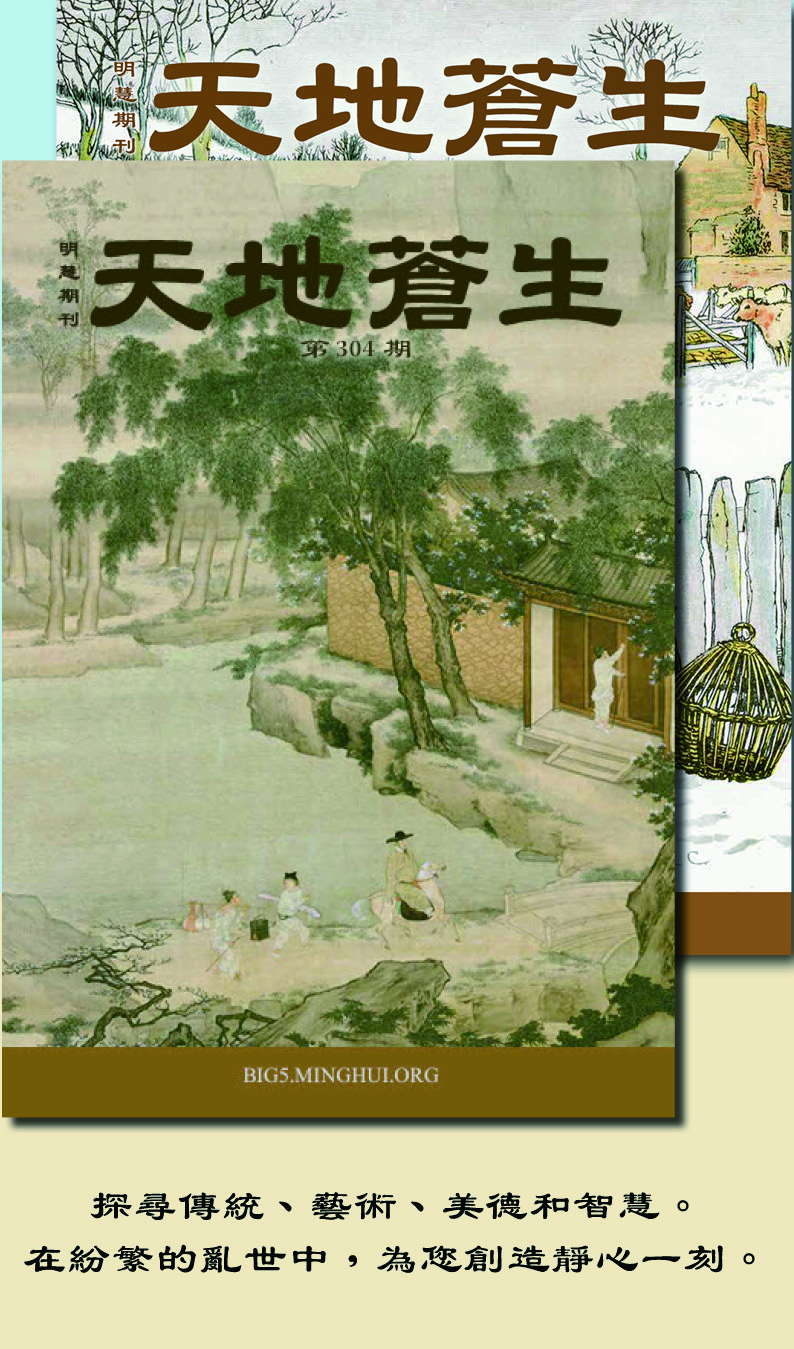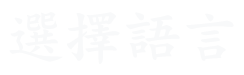雅樂的源起、變遷與回歸(2)
(接前文)
晉平公僭越遭天譴
在《太平廣記》中記錄這樣一個故事。師曠,是一位神異之人,人們不知道他出生的年代,也不知道他祖居在哪兒,也不清楚他的活動情況。到了東周晉平公時,師曠因為精通陰陽學而聞名於世。為了杜絕世人的疑慮,他將自己的眼睛薰瞎。
晉平公設宴招待衛靈公一行。酒興正濃時,衛靈公說:「我來貴國的途中,聽到一種新樂,想演奏給您聽聽。」晉平公便讓師涓演奏。師涓還沒彈完,晉國樂師師曠就手按琴弦制止說:「這是亡國之音,不能再彈下去了!」
晉平公不解,師曠說:「這樂曲是師延作的。師延曾為紂王演奏這靡靡之音,後來武王伐紂時,師延抱琴投水而死。所以聽到這樂曲的人,他的國家也一定會衰亡!」晉平公說:「我就愛好音樂,就讓我聽完吧。」師涓便一直彈到曲終。
晉平公問師曠:「樂曲中還有比這更感人的嗎?」師曠回答「有。」晉平公要聽,師曠說:「您的修為不夠,不可以聽它。」平公執意要聽,師曠只得彈奏。彈第一段時,有仙鶴聚集;彈第二段時,仙鶴們鳴唱飛舞起來。
晉平公大喜,又問道:「還有沒有比這更感人的?」師曠說:「有。從前黃帝曾用它來大會鬼神,如今您的德義修養不夠,不可聽它。否則將招致災禍。」平公說:「我已經老了,所愛好的就是音樂,就讓我聽聽吧。」師曠無奈,只好彈奏起來。彈第一段時,白雲從西北天邊湧起;彈第二段時,狂風驟雨,廊瓦吹飛。晉平公嚇得匍匐在角落裏。
此後,晉國大旱三年,赤野千里,晉平公也從此一病不起。
同是一首樂曲,黃帝以天子之尊、演奏與天地同和的大樂來酬謝天地神靈,這是天人合一的得道之舉。而晉平公道德不及諸侯,卻執意要聽與天地同和的大樂,這種用聖人的音樂來滿足聲色之欲的行為,助長了人的私慾妄念,是對天地神靈的褻瀆,所以遭到天譴。
黃帝留下的《樂經》失傳,就是人們道德不斷下滑,把音樂僅僅作為娛樂的手段,而不是溝通上天的修為,《樂經》沒有存在的社會基礎,所以就失傳了。
俞伯牙悟道
在東漢音樂家蔡邕著《琴操》中記述伯牙學藝的事蹟。在春秋時代,楚國的俞伯牙,跟著名琴師成連學習彈琴。成連看他天份很高,便傾囊相授,經過了三年的苦學,伯牙的琴藝已經盡得師父的真傳了。可是彈奏起來,總覺的琴聲中還缺少了點甚麼。伯牙為此非常的苦惱。
有一天成連對他說:「伯牙啊!你所少的只是那麼一點神韻啊!但這是一種境界,是無法言傳的。我的師父方子春,住在東海的蓬萊島上,他可以幫你,我們一起去請教他吧!」
於是師徒兩人來到了海上的蓬萊島,這時成連因為要到別處去接方子春,便命伯牙在島上等著。然後「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一個人在孤島上,開始時只能在海邊踱來踱去,焦急的等待著師父回來。但怎麼也不見師父回來,可能找不到師爺吧。
他也就不著急了。每天日升月沉,潮起潮落,他的心平靜下來了。
「近望無人,但聞海上汩沒崩澌之聲,山林杳冥,群鳥悲號,伯牙愴然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在那一剎那,天地之蒼遠,大海之遼闊,驚濤拍岸,他覺得自己瞬間消失了,隨手鼓琴,或緩或急,或高或低,一切都隨之自然。
彷彿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天上的飛鳥在鳴唱著喜悅,大海的濤聲在呼嘯著深沉,遠處的山巒安靜而厚實,宇宙萬物自有節律、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當一個人忘卻自我,和於自然,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時,他的心神與天地韻律合而為一。
這時,身邊響起了熟悉的聲音,「伯牙,你得到了音樂的奧秘,好好修為吧!」成連回來了。原來,這裏根本沒「太師父」這個人。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有「師法自然」之說,《周易﹒繫辭》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自伏羲始,古人仰觀天象,俯察地理、綜覽山川景物中,已明白天地間存在著一種安靜而有力的主宰力量,當人修煉到沒有任何名利之心、沒有雜念,就能體悟到那種力量的存在。所以師法自然,不是師其形,而是師其「心」。
千百來,中國傳統音樂已融化為人們日常中的一部份,以樂輔禮,以樂施政,寓教於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治民安上莫善於禮。」傳統文化中把樂和禮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完整的禮樂文化體系。禮樂充盈於天地,合於陰陽,通於神明,高遠深厚,使人心向善,純化社會風氣,提升人們的道德水平。
(待續)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5/12/27/231860.html